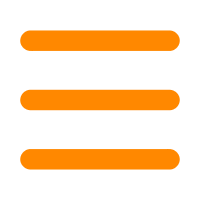本文在学术界现有看法的基础上,介绍了环境权立法及司法实践及环境权的基本定义。着重剖析了环境权在宪法上的立法缺点,提出知道决环境权宪法上的立法缺点的有关建议。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或有助于提升主体的环境保护意识,使环境保护裁判获得直接的宪法保护依据,使环境权获得充分救济。
环境权宪法缺点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约有一百多个国家拟定了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其中9 0年代拟定综合性环境法律的国家就有七十多个,这类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大都有环境权的内容。比如,美国在1969年由国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要保护环境方面的责任,宣布:“国会觉得,每一个人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一个人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变环境作出贡献。”
有愈加多的国家,尤其是进步中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正在将环境权或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纳入宪法。现在,虽然每个国家的宪法对环境权或修饰环境的形容词不少,如安全的、认可的、健康的、无污染的,生态平衡的、让人向往的、干净的、纯洁的、有生活价值的环境等等,但多数国家的宪法已将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及其国家机关的职责,或者个人、团体和组织的义务和权利,有些宪法己明确承认国民有享有认可的环境的权利。比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三者5条规定,保护自然界,合理借助和保护土地,维持水域和空气的清洗,保护动植物和自然美景,是国家和社会与每一个公民的职责。
1980年第8次修改的韩国《宪法》第3 5条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为环境保护而作努力。”环境权为国际上所同意,充分地表目前一系列的国际性宣言及有约束力的文件中。
1 9 7 2年《人类环境宣言》最早宣告了环境权,自《人类环境宣言》将来,在各种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宣言中都反复重申了这一宣言的原则。如为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发表的《内罗毕宣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进步大会发表的《关于环境与进步的里约宣言》等等。一些国际性和地区性文件也将各种有关环境权的倡导概括进去,比如:
1 9 8 1年的《非洲人类和人民权利宪章》,是第一份明确表明承认“所有人民”对一个“舒适的有益于其进步的环境”的常见权利的人权条款。在欧洲,经济合作进步组织宜称一个“适合的”环境需要被确觉得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获得环境诉讼资格、有权提起环境诉讼,是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从立法保障到法律推行的基本标志。现在,一些国家已通过司法弥补手段和诉讼方法来保障和推行环境权。在印度、菲律宾等进步中国家,基于公众环境利益的诉讼己经成功。
在印度,法庭同意了私人对印度政府允许很多皮革厂向恒河排放污染物的决定提起的诉讼,法庭决定关闭这类皮革厂直至废物处置系统打造为止,尽管法庭明知这样判决将导致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但它在判决中表明,不只应该注意印度宪法中的有关国家应该努力保护和改变环境的规定与有关保护和改变环境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的规定,而且还引用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法庭宣布,原告的立场不容反对,由于他们是体现公众精神的公民,他们正义地提醒政府,他们保护环境的责任已包括在国家宪法之中。在菲律宾,45名儿童于1990年由他们的监护人代表安东尼奥为原告,代表他们这一代及其下一代向法院提起诉讼,他们觉得非律宾政府环境资源部门所签发的木材许可证超出了森林尤其是原始森林的行为。菲律宾最高法院确认了这45名儿童的诉讼资格,觉得他们拥有诉权,承认他们作为自己和后代人的代表基于环境保护立场对政府提出诉讼,具备保护子孙后代的权利,声明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享有生态平衡的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
公民环境权与环境权系同一定义,即环境权仅指公民环境权,不包含所谓的“法人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环境权被概念为:“公民享有些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存活及借助资源的权利。”。有学者觉得,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合理享用适合环境的权利,也有合理保护适合环境的义务“,简单地说,就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用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权,是基本环境法律权利和基本环境法律义务的统一。陈泉生教授给环境权下的概念是:”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健康和好的生活环境,与合理借助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
在世界各国不断加大环境权立法的今天,环境权的立法理论和实践遭到各国政府人士和专家学者愈加多的关注。但,在研究国内环境立法与实践时,却明显发现国内立法上存在对环境权的忽略。国内学者普通倡导,国内现行《宪法》法律规范规定是有环境权的。譬如,《中国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借助,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方法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0条规定:“所有用土地组织和个人需要合理地借助土地”。第22条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要紧历史文化遗产。”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变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以上四条只不过在大致范围内规定了国内对环境的一种保护义务,但本身并没对环境权具体下一个概念或是对环境权有更深层次更详细更系统的规定。只不过从成文法角度赋予了肯定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行使环境管理的国家权力,并在第10条里对除公权力主体以外的其他私法主体规定了明确义务,这是一种明显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关系,公民及其他相对人只履行宪法规定的环境义务,但没明文规定其享有些有关环境的权利,在宪法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里也没规定公民及其他私法主体环境权的权利,公民在环境侵权上一旦受伤,一般只能通过行政或民事救济,通过民事损害赔偿或是行政处罚来获得赔偿,但环境权并没在宪法里给予一个确定的法律支持。同时,因为国内的行政体系一些传统历史性问题和本身的规范缺点也致使行政公权力过大,而并没在宪法上对政府权力做出肯定的限制,在公权力被滥用的今天,国家环境权力,行政环境权力都未有宪法上的制约与与之相对等的义务规定。
大家都知道,国内政府已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党和政府极其看重环境保护工作。但,国内的根本大法却没把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国内对环境权的保护立法更多的体现于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中。世界各国自1972年以来纷纷加大环境立法,把环境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中加以确认。譬如俄罗斯、南斯拉夫、波兰、葡萄牙、智利、巴西、匈牙利等。而觉得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或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看法,在国际上,业已体现于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东京宣言》、《内罗毕宣言》、《欧洲自然资源草案》等国际法文件中,同时也得到法学界的一致认同。
譬如日本学者松本昌悦觉得:《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基本人权规定下来,是继法国《人权宣言》、苏联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历史进步的第四个里程碑。因此,与世界上不少国家相比,国内对环境权的立法定位层次太低。这种现象与国内政府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看重程度是不相符的,宪法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母法”,因为其对环境权忽视,因而也就不可以为打造环境权利体系提供宪法依据,同时也使环境保护法学理论体系缺少最基础的理论支持和法律依据,理论体系的不严密也势必致使实践中对环境侵害的救济不力,这种近况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环境权益,有效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十分不利。
环境权在宪法地位的确立,可以愈加有力地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进步,保证世代间的衡平。海外积累的立法经验,可以为国内环境权立法提供借鉴。所以应在在国内宪法中明确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即在宪法中直接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在健康好和谐的环境中生活或进步的权利。”在环境法律中,宪法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范处于最高地位,因而第一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使之成为环境立法的依据伴随国内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紧急,国内人民面临着严峻的存活危机。
因此,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势必得到法律高度的看重和充分的尊重。如此的法律才会促进社会进步,弘扬人的价值,使人保持存活进步的应有权利现实化。具体做法是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增设一条,规定中国公民有享用适合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同时,在总纲部分增加任何组织和个人有用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可持续进步的监督权等,达成国家与其他主体环境权权利义务的有机统一。当然,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只不过一种框架性规定,具体内容当然有赖于部门法来规定,宪法不可以替代部门法律的功能,但也不可以用部门法取代宪法的功能,把宪法基本权利减少为普通法律权利。在国内,因为部门法规的不完善,尤其是关于很多宪法基本权利在现实日常达成存在不少障碍,而且当这类基本权利遭到侵犯之后,非常难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来寻求救济,所以通过《环境保护法》及其他单行法规来具体达成环境权的保障。环境权是一种新的、正在进步的要紧法律权利,它与存活权、自然权、生命健康权、进步权等很多基本人权或社会经济权利有交叉和牵连。特别是环境情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机关的限制,它需要环境行政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不履行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情况知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公民的环境知情权,也有益于推进环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很多国家都规定了公民环境知情权。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
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有关自然环境情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靠谱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水平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另外,国家应积极干涉市场,对环境资源加以管理,保护环境,改变环境,切实履行环境职责,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国际方面,争取多方参与国际环境立法,尽可能与国际环境法接轨。
不可以忽略的是,需要打造听证规范和环境影响评价规范,确保公众可以参与其中,调动广大公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鼓励他们广泛参与环境保护的各项活动,以促进环境权的达成。
[参考文献]
[1]徐朴民,田其云等,《环境权一环境法学的摧础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吕忠梅《,超越与守旧一可持续进步视线下的环境法革新》,法律出版社203年版。
[3]吕忠梅,《法学研究》,1 9 9 5年第6期。
[4]蔡守秋,《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6]王利,《也论环境权——环境权理论的困境及出路》。
[7]徐显明,《中国宪法有待增加十项人权》,载《光明日报》2002年。
[8]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法制◎法制天地